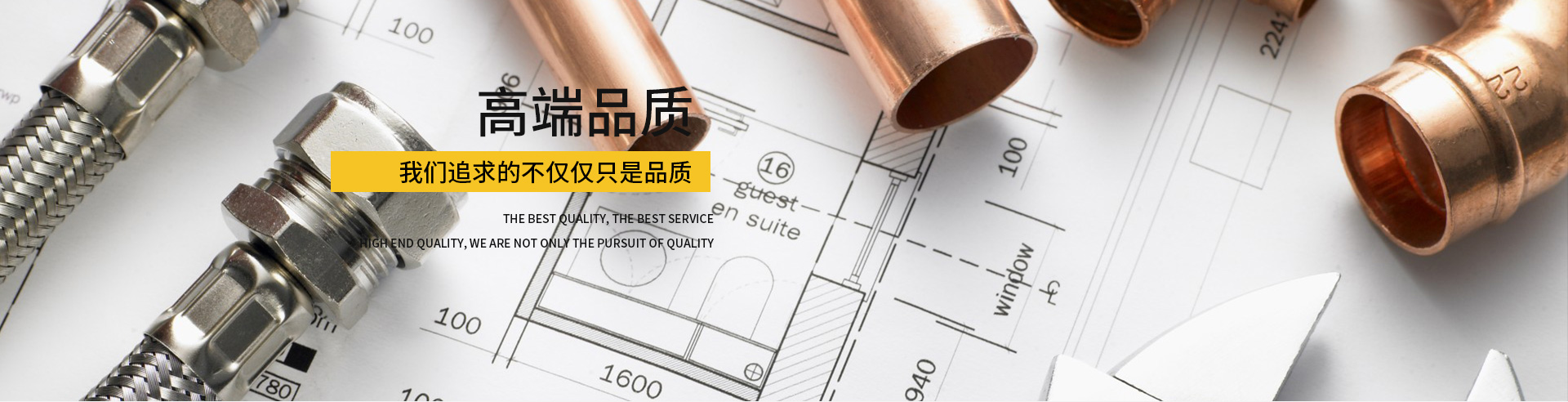日本占领者对待荷兰妇女的方式充满了诡计,有
发布时间:2025-10-29 11:03
 日本占领者对待荷兰妇女的方式充满了诡计,有些流氓,令人毛骨悚然! |东京 |女性安全 |日本侵略者 |荷兰 |集中营_网易移动
日本占领者对待荷兰妇女的方式充满了诡计,有些流氓,令人毛骨悚然! 1939年,日军打着“亚洲解放者”的旗号进入荷属东印度群岛(现印度尼西亚)。当地人曾一度将它们视为驱逐欧洲殖民的希望,但三个月之内,他们的幻想就破灭了。荷兰人被投入集中营,印度尼西亚人被奴役。最悲惨、难以言说的,是被称为“白人女性”的荷兰女性所经历的——这不仅是性暴力的盛行,更是制度化耻辱和人类堕落的剧本。这个剧本不是随意写的,而是有组织、有指导、有系统地推进的。编剧是日本资深人士这些军官;其高管是军官、军警,甚至还有军医;它的舞台是集中营、救济站、军营、封闭的私人住宅;其受害者是数百名被强行带出集中营的荷兰妇女。他们有的正值青春年华,有的已经有了孩子,有的则是教师、护士、钢琴家。但在日军眼里,它们“只是战利品”。 1942年3月日军占领巴达维亚(现雅加达)后,大批荷兰平民被监禁,男子被送往战俘营,妇女儿童被集中关押。最初的下一步是“照顾”,但很快这种“照顾”就变成了直接的控制和羞辱。在爪哇岛安巴劳村,集中营里的每个睡铺只有60厘米宽,一间屋子里塞着几十个人,食物是糊状的米汤,疫情大范围蔓延。每天早上七点点钟时,女性必须面朝东北,行三鞠躬,以示对日本天皇的忠诚。迟到或动作不规范的,将受到公司处罚。伯特·科菲努斯的母亲因鞠躬太晚而遭到军警殴打,直至手臂被折断。几个月来他都无法举起手。当时他只有14岁。他亲眼看着母亲被鞭打成泥,无力再反抗,更可怕的是,日军的惩罚不是落在有罪者身上,而是落在他们的亲人身上。如果孩子哭闹,母亲会被罚蹲几个小时;如果老太婆不肯跪拜,她的孙子就会被带走。 1944年初,日军在爪哇、泗水、三宝垄等地建立了所谓的“总救济站”——这些地方专门用于驱逐欧洲妇女,尤其是荷兰妇女。他们是从集中营被带走的最初被告知要“工作”或“担任护士”,但抵达后他们明白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性奴役。三宝垄的“七海之家”是最著名的舒适站之一。 1944年2月,约100名荷兰妇女被护送至此。进入大门后,他们的mga身份就被彻底去除了。所有东西都拍了照片并编号,照片贴在门上。墙上写着“使用规则”:每次不超过30分钟,每人每天最多20人,每周体检一次,孕妇立即处理。 18岁的玛尔特曾在集中营担任教师。被带到这里后,他的第一次“检查”就是被军医性侵。他被迫接收日本军官和士兵。他们日夜迷茫,浑身阴云密布。他们感染疾病后得不到治疗,只能等待死亡。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对未成年人的迫害。 13岁的莉亚因为长相漂亮而被警察“记录”。他试图阻止,但被告知如果他不服从,他的全家都会被杀。 “白马事件”又是一个地狱。 1944 年中期,三周内有 30 多名欧洲妇女被监禁。日军称他们为“白马行动”,每天晚上都被这个名字“利用”,严刑拷打。它们没有名字,简单地称为“白马一号”和“白马二号”。沃赫莱奈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试图剃光头、毁容脸,让自己看起来“一文不值”,但这种反抗被认为是“另类新奇”,他遭受了更多暴力。就连军医也参与其中。它不再是“回顾”,而是“体验”。他的证言将成为未来东京民事法庭的重要证据。战后,约250名荷兰妇女向荷兰政府登记为“幸存慰安妇”,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真实数字远高于此,很多人选择保持沉默,不是出于遗忘,而是出于羞耻。简·鲁夫-奥赫恩 (Jan Ruf-O'hern) 是少数站出来的女性之一。 2000年,他在东京民事法院出庭作证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,但他却坚定地说:“我不是要报复,我只是想承认发生的事情。”他的证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面前播放。玛尔特从未结婚,晚年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。日本政府尚未完全承认其对荷兰妇女福利体系的责任。 2015年,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将“慰安妇档案”纳入世界名录纪念时,日本强烈反对,并停止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历史的沉默并不意味着真相不存在。这些荷兰妇女的命运是战争最黑暗的注脚。他们不是军人不是政客,而是无辜的平民。然而,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下,他们的身体成为了战场,他们的尊严成为了牺牲品。他们的故事不是为了仇恨,而是为了警告:当人类社会允许非人道对待“敌人”时,文明的底线就崩溃了。参考文献 [1]《荷兰战争罪法庭记录·斯马兰案》,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档案,1948年。
特别声明:本文由网易自媒体平台“网易号”作者上传发表,仅代表作者观点。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
注:以上内容(包括图片和视频,如有)由网易HAO用户上传发布,网易HAO为社交媒体平台,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。
日本占领者对待荷兰妇女的方式充满了诡计,有些流氓,令人毛骨悚然! |东京 |女性安全 |日本侵略者 |荷兰 |集中营_网易移动
日本占领者对待荷兰妇女的方式充满了诡计,有些流氓,令人毛骨悚然! 1939年,日军打着“亚洲解放者”的旗号进入荷属东印度群岛(现印度尼西亚)。当地人曾一度将它们视为驱逐欧洲殖民的希望,但三个月之内,他们的幻想就破灭了。荷兰人被投入集中营,印度尼西亚人被奴役。最悲惨、难以言说的,是被称为“白人女性”的荷兰女性所经历的——这不仅是性暴力的盛行,更是制度化耻辱和人类堕落的剧本。这个剧本不是随意写的,而是有组织、有指导、有系统地推进的。编剧是日本资深人士这些军官;其高管是军官、军警,甚至还有军医;它的舞台是集中营、救济站、军营、封闭的私人住宅;其受害者是数百名被强行带出集中营的荷兰妇女。他们有的正值青春年华,有的已经有了孩子,有的则是教师、护士、钢琴家。但在日军眼里,它们“只是战利品”。 1942年3月日军占领巴达维亚(现雅加达)后,大批荷兰平民被监禁,男子被送往战俘营,妇女儿童被集中关押。最初的下一步是“照顾”,但很快这种“照顾”就变成了直接的控制和羞辱。在爪哇岛安巴劳村,集中营里的每个睡铺只有60厘米宽,一间屋子里塞着几十个人,食物是糊状的米汤,疫情大范围蔓延。每天早上七点点钟时,女性必须面朝东北,行三鞠躬,以示对日本天皇的忠诚。迟到或动作不规范的,将受到公司处罚。伯特·科菲努斯的母亲因鞠躬太晚而遭到军警殴打,直至手臂被折断。几个月来他都无法举起手。当时他只有14岁。他亲眼看着母亲被鞭打成泥,无力再反抗,更可怕的是,日军的惩罚不是落在有罪者身上,而是落在他们的亲人身上。如果孩子哭闹,母亲会被罚蹲几个小时;如果老太婆不肯跪拜,她的孙子就会被带走。 1944年初,日军在爪哇、泗水、三宝垄等地建立了所谓的“总救济站”——这些地方专门用于驱逐欧洲妇女,尤其是荷兰妇女。他们是从集中营被带走的最初被告知要“工作”或“担任护士”,但抵达后他们明白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性奴役。三宝垄的“七海之家”是最著名的舒适站之一。 1944年2月,约100名荷兰妇女被护送至此。进入大门后,他们的mga身份就被彻底去除了。所有东西都拍了照片并编号,照片贴在门上。墙上写着“使用规则”:每次不超过30分钟,每人每天最多20人,每周体检一次,孕妇立即处理。 18岁的玛尔特曾在集中营担任教师。被带到这里后,他的第一次“检查”就是被军医性侵。他被迫接收日本军官和士兵。他们日夜迷茫,浑身阴云密布。他们感染疾病后得不到治疗,只能等待死亡。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对未成年人的迫害。 13岁的莉亚因为长相漂亮而被警察“记录”。他试图阻止,但被告知如果他不服从,他的全家都会被杀。 “白马事件”又是一个地狱。 1944 年中期,三周内有 30 多名欧洲妇女被监禁。日军称他们为“白马行动”,每天晚上都被这个名字“利用”,严刑拷打。它们没有名字,简单地称为“白马一号”和“白马二号”。沃赫莱奈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试图剃光头、毁容脸,让自己看起来“一文不值”,但这种反抗被认为是“另类新奇”,他遭受了更多暴力。就连军医也参与其中。它不再是“回顾”,而是“体验”。他的证言将成为未来东京民事法庭的重要证据。战后,约250名荷兰妇女向荷兰政府登记为“幸存慰安妇”,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真实数字远高于此,很多人选择保持沉默,不是出于遗忘,而是出于羞耻。简·鲁夫-奥赫恩 (Jan Ruf-O'hern) 是少数站出来的女性之一。 2000年,他在东京民事法院出庭作证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,但他却坚定地说:“我不是要报复,我只是想承认发生的事情。”他的证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面前播放。玛尔特从未结婚,晚年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。日本政府尚未完全承认其对荷兰妇女福利体系的责任。 2015年,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将“慰安妇档案”纳入世界名录纪念时,日本强烈反对,并停止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历史的沉默并不意味着真相不存在。这些荷兰妇女的命运是战争最黑暗的注脚。他们不是军人不是政客,而是无辜的平民。然而,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下,他们的身体成为了战场,他们的尊严成为了牺牲品。他们的故事不是为了仇恨,而是为了警告:当人类社会允许非人道对待“敌人”时,文明的底线就崩溃了。参考文献 [1]《荷兰战争罪法庭记录·斯马兰案》,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档案,1948年。
特别声明:本文由网易自媒体平台“网易号”作者上传发表,仅代表作者观点。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
注:以上内容(包括图片和视频,如有)由网易HAO用户上传发布,网易HAO为社交媒体平台,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。 下一篇:没有了